我妈改嫁了。
推开门,遇见季屿川的瞬间,我的心跳停止了,脑子里空白一片。
高考后他向我告白,我平静而冷淡地看向他。
“我很讨厌你。”我说。
他似是被定住了一秒,随后便自嘲地笑了笑,试着去掩饰这份难堪。
我看着他眼里的光一点一点地缓缓熄灭,松开的拳头如同一首碎裂的情诗。
少年垂下眸,走远了。
暗黄的街灯下,小雨淅沥而至。
那个落寞的背影,连同那些胆怯、羞涩与隐秘的期待,日积月累,沉成了这些日子里我难以治愈的内伤。
我的偏见亲手打碎了一个少年的炙诚喜欢,这是罪过。
如今,我住进了他家,以继妹的身份。
1.
季屿川帮我把行李搬进了房间,我住在他的对面,与往常在家的卧室位置相反。
“谢谢。”我说。
他简单地应了声,随后便开始往回走。
我犹豫了瞬间,还是跑过去拉住了他的手,将盒子递了过去。
“季屿川,天冷了,织给你的围巾,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。”
这是替四年前的我,亲自道歉的意思。
那话说得太伤。
季屿川身体一僵,顿住了。
然而他只是抬眸看了我一眼,眼神疏离。
他拂开了我的手:“不用了,用不着。”
“那……不好意思。”
我缓缓地将盒子收回,朝他僵硬地微笑了一下。
关了门,躺在床上,一下一下地抚摸着围巾柔软的绒毛,我将头埋在枕头里,心情在冰凉的海里浮着,浸了一身的苦涩。
夜深了。
我们形同陌路。
母亲敲了敲门,端了两杯热牛奶进来。
她说,这阵子她要和季父去国外出差,一两个月都回不来,让我好生照顾自己,跟季屿川好好相处。
我望着另一杯牛奶,点了下头。
许久,门才开了。
季屿川刚洗完澡,单围着条浴巾,上半身裸着,头发还是湿的。
脸有些发烧,我握紧了手中的牛奶:“趁热喝,别着凉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晚安。”我轻声说道。
季屿川接过杯子,指尖擦过我的掌心。
微烫的余温,印了下来。
我心头溅开一朵悸动。
2.
半夜,我被姨妈痛醒了。
吃了止疼药,去了躺厕所,摸着黑晕晕乎乎地往回走。
卷起被子,窝在里头,蜷缩着身子,痛着痛着便睡熟了。
次日醒来,发现自己躺在季屿川的床上,抱着他的枕头,紧紧扣在怀里。
抬头望去,他躺在落地窗前的沙发上,只盖一层薄薄的毯子,半边身子敞在空气中。
我皱了皱眉,将毯子拾起给他盖好。
他醒了,目光与我对上,挑了下眉。
我心头一颤,退了三步。
他眉间微蹙,手一伸,将我拉进怀里,不悦道:“光着脚,很热?”
冷不防地被吓住,我一个重心不稳,跌到他身上,双手无处安放,只好顺势撑在他脖颈两侧,睡裙不经意间擦过他的鼻尖。
“不好意思。”
“嘘,别动。”
“嗯?”
“听,敲门声,我爸,好了,门马上就要开了。”
说着,季屿川猛地一个翻身,毯子一拉,将我迅速扣至身下,摁到他怀里。
浓烈的男性气息铺面而来。
带有一种清冷的性感。
我双手抓住沙发,呼吸有些紊乱。
彼此之间的衣服很重地摩擦了一下。
隔着薄薄的面料,他的身躯温柔地吻过我的肌肤,如同羽毛轻轻滑过。
我微微一颤。
季屿川扣住我的腰,低喝道:“别乱动。”
腰间似蚂蚁爬过,我错开了眼神,绷紧了身子。
“季屿川。”
“嗯,小声点儿。”
我咬了咬唇,抠住沙发。
“诶,我怕痒。”
季屿川低头看了过来,眸里的光往深处沉了下,他喉结动了动。
“等会儿。”
“嗯。”
他的嗓子还未完全醒来。
声音哑着。
沙沙的质感顺着我的颈部一路慢慢往下犁,我的整条脊椎骨趋于酥麻,头皮和耳朵一阵一阵地过电。
脚趾蜷起,我用腿部费力地抵住沙发沿,大气不敢出。
“屿川,怎么睡沙发呢?”
“昨晚失眠,看了会夜空。”
“我和沈阿姨去机场了。”
“嗯。路上注意安全,我在沙发上睡个回笼觉,阳光暖和。”
“这两个月别老出去瞎逛,在家好好照顾听澜,有什么要紧事再说。”
“嗯。”
季叔叔离开了。
季屿川迅速起了身。
我出了一身的汗,因为紧张。
“疼不疼?”
季屿川看着我被他按红的肩部,低声问道。
我摇了摇头,掀开了被汗水黏在颈部的发丝。
“昨晚不好意思,我走错房间了。”
“没事。”
“那,床单、被套,我帮你换着洗了?”
我走过去,拉开了拉链。
季屿川起身拽住我的手腕。
像鱼尾游过甩下的水花,他漫不经心的尾调在我耳边响起。
“干干净净的,洗什么?”
3.
半个月,我都待在房间里看书,看累了,便泡杯茶在阳台上静坐一会儿,看着泳池里清澈的水在阳光下闪着金花,看着鸽群从千家万户的屋檐前飞过。
季屿川也很安静,他很少出门,大多时候都在书房,我们几乎只有一日三餐有交集,平常也不怎么说话。
日子过得很慢,碗筷相碰的声音反刍出一种更为明亮的寂静。
严洛宸来了,许之瑶也来了,阿姨中午多做了些饭,都是些家常菜。
今天比往常多了几道辣菜:麻辣兔头、辣炒鱼片与红油菠菜,中间一个鸳鸯锅,辣锅里放了些肥牛。
色彩明艳,温度热烈。
这是应许之瑶的要求,我看着有几分吃味。
“新来的妹妹?”严洛宸看着我说道。
“嗯。”
“很甜,乖乖软软。”许之瑶笑着说道。
她是明媚的妆容,烫着大波浪卷,极尽张扬。
我第一眼看上去却生不出好感。
那双眸子里藏着敌意,不明净。
季屿川抬眸看了我一眼,夹起一个麻辣兔头,淡道:“不甜,是这个味。”
严洛宸轻笑了一声:“想起来了,妹妹是校花,表白墙上有不少人捞,怪不得眼熟。目前有在谈对象?”
季屿川筷子一顿。
我讪讪地笑了笑,摇了摇头,一小口一小口地泯着汤。
“饿死鬼投胎。”
季屿川把手搭到我的椅子背上,低嗔了句。
说完,夹了点培根芦笋卷放在我的碟子里。
我轻踢了他一脚,踢完又立马后悔了。
那边却收了一个力道,往回勾住我的脚:“桥牌三缺一,一起?”
“嗯。”
“哎,往常不都是玩斗地主吗?怎么就今天玩桥牌呢?”
许之瑶嘟囔了句,我看着她将余下的肥牛尽数倒进辣锅,心下不悦。
“你们玩吧,我午后小憩一会儿。”
许之瑶跟没听见似的,若无其事地将盘子里的乌鸡卷全倒进辣锅。
嗯,真是好家伙呀。
刚刚我说,留两三片在清汤里,我不吃辣,原来是竹篮打水。
这是你家?
我笑着看了许之遥一眼,若无其事地舀了一小勺田鸡。
她就站了起来,用自己的筷子夹了几片肥牛,跃过我的手,径直递到季屿川的碗里。
礼节可真是周到。
那辣汤刚好滴到我的手背上。
我挺怕疼的,手一抖,差点弄翻了半勺。
许之遥她好像没看到。
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
我心下冷笑了声,用公筷将季屿川碗里的肥牛夹出,将那半勺田鸡舀给了他。
“哥哥最近口腔溃疡了,吃不了辣。”
话音刚落,我明显感觉到落在我椅背上的那只手力道加大。
许之遥目光一滞。
一顿饭,吃了个不尴不尬。
4.
午后醒来,我躺在客厅里的摇椅上,放了点舒缓的曲子。
阳关从帘子的缝隙里漏了进来,那只挪威森林猫跳进了窗子,窝在了我怀里。
我捏了捏她的脸颊,她眯着眼睛舒服地仰起了头,蹭了蹭猫柔软的颈部,我顺着她的背部轻轻地划拉。
许之瑶走了过来,敲了敲壁柜。
我捉到了她眼里的一丝拧巴,笑了两声。
“怎么呢?”我问。
“喂,你要不跟我们一起打桥牌?”
我停下了手中的动作,扬了扬眉。
许之瑶的目光跳过我的眼睛,看向后边的壁画。
“其实……其实我们三个人斗地主也没啥意思。”
她支支吾吾着,两只手不断地绞着自己的腰带。
我看着她紧绷的嘴角,心下了然。
她在季屿川前吃了瘪。
我起了身。
棋牌室单亮着盏月光银水晶灯,照在那张玉石蓝方桌上,淌出幽幽的光。
季屿川仰倒在椅子上,眼眸微阖,眼底淡淡鸦青色,睫毛打下一线暗影,有几分颓痞的意思。
我进来的瞬间,他视线探了过来,目光一触即离,落在我怀里的那只猫上。
前方剩着西位和南位。
我坐到他旁边,点了下头:“不组队,对打。”
季屿川拿着扑克的手一紧。
沉默了半晌,他才缓缓说道:“猫,就先放下吧。”
5.
严洛宸与我为南北方,季屿川同许之瑶为东西方。
双方打友谊定局赛,按国际比赛分结算,辅以贴点计分法。
第一副牌双方有局,东西方完成大满贯定约;
第二副牌东西有局,南北方完成小满贯定约。
第三副牌……
我卡在了季屿川手里。
他布了个网,将我拉到深水区,慢慢磨。
不一刀致命,而是一环一环地下套,将我钓到鱼钩上,不停挑逗,若即若离。
拖着泥又带着水,藕断丝连。
我皱了皱眉,甩了张黑桃出去,许之瑶出两个红心。
严洛宸会意,出两个黑桃,季屿川被动出三个红心。
鱼钩倒转,主动权回到我手里。
我打算……
玩一场猫捉老鼠。
季屿川将会是这只鼠。
叫下“4个黑桃”,我成为庄家,西家首攻,出黑桃Q,北家为明手,亮牌。
季屿川的眼神向我正面迎了过来,甩出几张牌。
超额一墩打成3梅花无将,得430分,折合10国际分。
东西联手牌25个大牌点,超平均数5个,扣5分,得5分。
我打出两个黑桃,超额一墩,得140分,折合4个国际分,扣除1个大牌分,得3分。
季屿川眼里的兴味浓了起来,他轻呷了一口水,眸底沉下一层狠厉的侵略性。
他打出6个梅花一宕,朝我挑了挑眉。
目光弦上相遇的瞬间,我的心跳加速了几分。
如同走在刀锋上,生出一种危险的刺激。
季屿川是个悬崖狂客,惯会悬崖勒马。
打法激进,但漂亮得很。
而牌局中,我恰好喜欢有惊无险,与层出不穷的意外。
示意了下严洛宸,我们决定转守为攻。
“严洛宸,弃方块树梅花。”
“严洛宸,要不我们守攻吊将?”
“严洛宸,我们吃第4轮方块?”
……
我和严洛宸的指尖不自觉地越靠越近,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的温度。
季屿川的目光落在我们的手上,脸上的玩世不恭陡然收住,像一把伞唰地合拢。
他的牌风瞬间凌厉了许多,暗藏寒芒,简直可以看到其中的一把利刃。
双方打得很狠。
在狂飙之上拧紧盖子,猛踩油门,塞紧时间。
疾驰在暗礁险滩的冒险之中。
转攻,险着,断掉的桥,困兽犹斗,抓捕,诡计,阴谋,无仇的圈套,磨,你死我活。
南北方赢了十墩,东西方拿下三墩。
东西方赢下八墩,南北方拿了两墩。
南北方打下大满贯另加5分,东西方打成小满贯另得3分。
十六副牌结束得很快。
44:43。
“你输了。”
我走到季屿川对面,双手撑在桌子上,眉目张扬恣意,挑衅地看着他。
一瞬间,季屿川眼里的平静碎裂了,如墨的眼底暗流涌动,似一匹饿狼。
他一个翻身从桌上跃了过来,把我摁回椅子上,搂住我的脖子,坐在我的腿上。
他用风衣兜住了我们的脸。
黑暗中,他单手挑起了我的下巴。
径直吻了过来。
狂暴热烈,如疾风骤雨。
6.
我无法平静下来。
内心躁动不安。仿佛围困在周围空气虚妄的谵语之中,被沙漠里干热混沌的蒸气笼罩着,一阵一阵地发着低烧,忽冷忽热。
我坐立不安,手里的书一个字也没看进去,企图用睡眠麻痹自己,可是一闭眼,却发现,脑子里全是与季屿川有关的画面。
他眸中的狂热,力道的野蛮。
以及眼尾的克制。
我披上外套,走到二楼的露天阳台。
远远地便看见季屿川站在雕花护栏前,手里燃着一根雪茄,火星子随着晚风忽明忽暗。
他还穿着刚刚商谈的那身西装,许是刚回来没多久。
桥牌结束不久后他就去华城证券总会了。
清冷的月光照在他身上,他一半隐在阴影里,一半从深海里走了出来,带上一丝邪气,无意间给黑夜布了一道饵。
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男人。
一种如同蛰伏的海兽,幽邃魅惑,跃出水面的瞬间,银色的月光淌了一身,闪闪发亮。
另一种像骆驼,踏实厚重,拿着粗粝的温暖酿了很浓的家味,腌出炭火里酽酽的绵软与舒适。
季屿川是前者。
藏着一种逾矩、危险的引诱气息。
冷冽的晚风萃不去心中的郁热,我开始往回走。
那边出了声,声音从月光的鳞片中穿行而来,匀了一 层银脆的质感。
“睡不着?”
“嗯。”
“躲我?”
“……没有。”
季屿川低头掸了掸指尖的烟灰,他松了领带,解开了领口的扣子,走了过来。
有淡淡的冷香、烟味与Liber Pater的酒香。
我往后退了几步。
“别动。”
他从旁边的花坛折了一朵雏菊,别在我外套翻领的扣眼里,微凉的指间从我颈肩滑过。
像鱼吻,冰凉而颓废的吻。
“准备一下。”他说。
“嗯?”
“下个月宋氏财阀太子的订婚宴。”
“不去……”
季屿川食指抵在我的唇上,截断了我要说的话。
他侧过头俯在我耳边说道:“跟宋珩很熟?”
“谈过一段时间。”
“多久?”
“三个月。”
季屿川的眸色一沉。
他安静地看着我,目光如同隐伏水底的暗礁。
许久,他递来一份红色烫金请柬。
沈听澜小姐芳启。
几行行楷在清冷的月光下一点一点地浮了上来。
7.
一下车,司机便给我递了件极为厚实的披肩。
我看着那大得足以裹住全身的面积,不自觉地皱了皱眉。
“不用了,里边不冷。”
季屿川走了过来,淡道:“怕见前男友失了风度?穿着。”
“不过是有些闷罢了。”
说着,我一边松了领口的那粒盘扣。
季屿川的目光拂过我的身体,沉默了片刻,他开口道:“不许弯腰,不许喝酒,不许……同别的男人调情。”
我手下一顿,稍微抬了抬眸看向他,接过司机手中的伞:“为什么管我?”
“阿姨叮嘱的。”
“哦。”
我垂下眸不再看他,将步子走得快些了,同他拉开些距离,到了前头。
高跟鞋落在青石板上发出哒哒的响声。
只不过音竹给设计的是套妃色毛呢旗袍,多少有些限制速度。
季屿川几步便迈到了我的身侧,他用手背碰了碰我,语气有些不悦:
“就这么急着去见宋珩?”
“怎么?你管我?”
“知不知道下了雪路滑?况且音竹把衣服设计得很……”
“很什么?”我侧过眸朝他看去。
季屿川没说话了。
他静静地注视了我两秒,打横把人抱了起来:“摔倒了可别麻烦人。”
“不会麻烦你。”
“别闹。”
季屿川攥住了我的双腕。
这时,宋珩从里边走了出来。
他点了下头,目光顺着季屿川看去,在他环住我腿窝的那只手上停了几秒,握住伞柄的拇指滑了下。
“不赶时间,慢慢走,可以把听澜放下。”
他的语速很缓,每一个字,都像是从冰雪里析了出来,闪着一种釉质的寒光。
季屿川抬眸,淡淡地扫了他一眼,收在我腰间的手紧了紧。
空气中生长着有一种很静很锋利的弦波。
一只乌鸫从油杉树梢掠过,尾羽闪过蓝色的幽光。
雪裂下来,白日寂寥。
季屿川的手忽而松了下手,不着痕迹地滑过我的腰线与臀线。
有些敏感。
我不由得低吟了一声,更紧地蜷在他怀里,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。
“季屿川,你这是干什么?”我压低声音嗔道。
“掂一下试试,看着不瘦,怎么这么轻?”他用更低的声音伏在我耳边说道。
我的脸不自觉地红了。
“哪有,诶……你先放我下来。”
“还是不了,这样抱着比较暖和。”
一旁,宋珩握紧了手中的伞,脸上似乎有了几分冷意。
“风大了天凉,那便先进去吧。”他说。
8.
订婚宴排场并不算大,只请了两家的亲戚。
新娘是我认识的,关家的千金,关茜。
刀切豆腐两面光,蛇蝎美人一个。
巧的是,他们敬完酒后便坐到了我们这桌,关茜就坐在季屿川身侧。
“季少,喝一杯啊,多少给个面子。”
她笑着朝季屿川说道,眸子似醉非醉,像几道软绵绵的钩子,将人黏住往里收,藏了几股狠劲儿,临门一脚,妩媚酿到底。
季屿川淡漠地扫了她一眼,端过我的酒杯,一饮而尽:
“祝新婚喜成,笙箫和鸣。”
关茜端着酒杯的手一僵,随后摆出笑容来:“还是季少会说话。”
她娇嗔似地想把手往季屿川肩上搭,季屿川一避,靠到我肩上。
我手中的筷子没拿稳,直直往地下落去。
这一瞥,却见关茜的腿勾住了季屿川的脚踝暧昧地蹭了蹭,大有往他腿上攀的意思。
而季屿川却纹丝不动,如无事发生。
像是弦断了,我心中一怔,将椅子往后推了推,找了个借口去了趟盥洗室。
洗了洗手,准备就此离去时,没料到宋珩就倚在外头的墙上,我冷不防地被惊了一下。
手机掉到了地上,宋珩的打火机也掉了下来。
我弯下腰捡起。
他轻轻地咳了下。
我皱了皱眉:“拿好了,没事少抽点烟。”
宋珩轻笑了两声,指节上的薄茧微微刮过我的掌心。
“沈听澜。”
“嗯?”
“怎么不来找我?”
“牙医又不止你一个。”
“啧,说话还是这么呛。”
“不要站在这里堵我。”
宋珩笑了笑,单手插兜。
“有没有人说过你很像一种酒?”
“什么酒?”
“香槟。初尝尚不觉得有什么,后劲却大得很。”
我没有理会他的话,提步想走。
宋珩将手撑到我身侧,低头道:
“看下牙?”
正要拒绝,余光中,我瞥见了季屿川的身影,索性闭上了眼。
宋珩轻轻钳住我的下巴,往前走近了一步,淡淡的烟味传来。
我能感觉到他注视了我好一会儿,许久,他才开了口:
“第二颗磨牙还没处理好,找时间去我那里检查下?”
“嗯。”
9.
回去的路上,我和季屿川一直没有说话。
司机把车驶进车库时,隐约可以看到客厅里亮着朦朦胧胧的光。
母亲和季父回来了。
他们在桌上留了张纸条,说他们先入睡了,礼物给我们放在沙发上,晚安。
吹好头发坐到床上,我看到季屿川先前发了条消息过来。
睡了吗?
没。
你那里方便洗澡吗?我这边的淋浴坏了,去西边的浴室担心吵到他们。
嗯,你来吧。
花洒下的水声哗哗地传来,我拿了本书坐在床头翻了翻。
心却静不下来,回过神来时,手中已经煮好了橄榄酸梅汤。
从盥洗室的走廊里回来后,季屿川喝了不少酒。
想到这些,不由得有些心烦意乱,我将书盖到脸上假寐。
“睡着呢?”
“嗯。”
季屿川笑了两声,将我脸上的书拿开。
“案上的汤煮给我的?”
“想得美,我自己喝。”
“你一个人能喝这么多?”
“今天喝不完我留着明天喝。”
季屿川没说话了,他在我身边躺了下来,肩膀几乎和我挨到一起。
我翻了个身背过去,他一手将我揽到怀里。
“想跟宋珩复合?”
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?我要睡了。”
“我以为你明白的。”
“明白什么?哦,明白你看着像‘处子’,原来却是个浪子,关茜的腿都快跟你叠在一起了,你怎么都不知道避开一下?你那天吻我几个意思?是临时起意玩玩还是……居然会如此的驾轻就熟。”
季屿川原本有些严肃,后来听着听着却笑开了,他俯身撑在我上面,肩膀轻轻地碰了我一下,低声道:“别这样,我会想吻你。”
“那你吻啊。”我气道。
季屿川果真吻了下来。
我很重地咬了他一口。
他倒吸了口气,舔了舔唇上的血珠:“好狠。”
我扭过头不再看头,扯过被子把自己给蒙住。
季屿川索性把我包住给整个地抱了起来。
“关茜现在应该在医院。”他说。
“在你没看到的地方”,季屿川说着顿了顿,“我把她的腿给弄骨折了。”
我沉默了一阵,没吭声。
他继续说道:“我未曾有过女人。至于那个吻……是在想象中千锤百炼,炼出来的。”
我脸一红。
“我爱你。”他紧接着说道。
我将被子往下拉了拉,露出了一小张脸。
季屿川睫翼颤了下,他衔住我的唇温柔地吻了吻,鼻尖抵住我的鼻尖:
“六年就前拒绝了,这回还打算拒绝?想都别想。”
10.
大寒假一过,季屿川便回Cornell去念硕士阶段的最后一学期了。
宋珩的婚也没结了。
只是他开始在华城大学授课,任命我为他的学生助理,并把工作地点换到了华城大学附属医院,偶尔会去上上班。
其实当时我们恋爱就是当了下彼此的工具人,为对方挡了下桃花。
他是我硕导带的直博生,我们师门聚会的时候认识的。
今天我们正在做实验时,季屿川打了个电话过来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在我以为信号中断时,他平静而庄重地宣布道:
“沈听澜,我今天回国。”
这语气里藏着有几分不易察觉的愉悦,像一帆于河面自由漂流的小舟。
我愣了几秒,哑然失笑。
那边又清了清嗓子,即刻出了声:“准备一下,我给你叫辆出租车,预定时间到机场等我。”
回过神来,我连忙道:
“不,我要自己开车来。”
说完,我扭头看向宋珩:
“待会做完实验就离开,好吗?”
宋珩手中的动作一顿,点了下头。
“好。”
他垂下了眸,看着眼前的仪器,眸子里滑过些悲伤。
整场实验做下来都非常安静,连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,不过我没怎么放在心上。
实验做完我便拿起桌上的钥匙,出门往外走。
此时已是晚上七点,街道华灯初上的光景。
航站楼里疏疏落落地站了些人。
飞机到站后,人群涌上。
我一眼便看到了季屿川,他穿着件淡茶色衬衫和米色长裤朝我挥了挥手,推着咖色的行李箱远远地朝我跑来。
我微笑着看着他,没来由得眼眶有些湿润,像是阔别经年。
“想你。”季屿川说。
他一来,便将我抱住了,吻了吻我的脸颊。
清冷的气息袭了我一身。
“嗯,不要,胡子好扎人。”我推了推季屿川。
他笑着:“饿了没?”
“嗯。”
“我们回家。”
11.
一路上,我把车开得飞快,走了条单行线,直接穿了过去。
路旁的树大片大片地往后撤,留下一路的风声呼啸。
我们骑了一匹野马。
“不怕查?”
“谁敢查我?”
季屿川忽而就笑了起来,侧过头来懒懒地看着我。
橘黄色的灯光掠过他的眼睛,他眸子里闪着些细细碎碎的光。
“沈小姐,请在驶进车库的小岔路旁停下车。”
“不停。”
“这位小姐,您再不停我该吐了。”
我缓下了车速,朝他狐疑地看了一眼。
他浅笑着,朝我理所当然地点了下头。
停下车,开了窗,路旁的小竹林摇曳着,发出哗哗的响声。
季屿川一时安静了下来。
淡淡的竹叶清香随着晚风缓缓飘进。
“听澜,过来,帮我解一下安全带。”
“不行,万一你吐到……”
下一秒,我低呼了一声。
季屿川他长腿一跨,直接爬到了我的座位,欺身而上。
随着座位被他“啪”的一声放下,季屿川顺着惯性又往前移了一步。
我闷哼了一声。
眼前,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。
目光在我唇上停了几秒。
“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?”他说。
说完,他一把将我的双手举过头顶,另一只手拐到了我的腰间,双腿跪在我腿侧,低头吻了过来。
先是很轻、很小心地吻了过来。
像是鱼潜渊,鸟归巢,一切都静了下来。
周围只剩下呼吸声的盛大开放。
我喘不过气来了。
忍不住揪紧了他的衣服,低吟了一声:“不要。”
季屿川手下一紧,加紧了攻势。
绵绵密密的吻像夏天的风鼓蓬蓬地拍过……
他的手也不安分了,开始游,游,游向我的衣内。
一,二,三……全解开了。
他的手缓缓向前游去,我情不自禁地发出轻轻的呻吟声,类似于:嗯。
季屿川咬开了我的扣子,他的呼吸变得越发地急促起来,指尖刮过我的皮肤。
我像片叶子般微微颤抖了下。
他掐住了我的腰。我轻嘶了一声。
车内的气温在不断上升。
这时,车外一束光打了过来。
一辆车驶近了。
12.
是季父的司机。
母亲和季父下了车。
季屿川和我在前一秒归了座,衣衫还有些凌乱,呼吸还有些急促。
借着路灯浅浅的光,我们四人彼此相望,沉默了一阵。
黑夜里,风的羽毛铺了我们一身。
母亲盯着我看了许久。
在我即将被风淹没的时候,她问道:“你的嘴唇,是被狗啃了?”
背地里,我使劲掐了一下季屿川,他把我的手包在了掌心。
季父在一旁笑了起来。
他说:“彩礼就先定为季节传媒公司、九曲山庄的花园别墅,外加一辆宾利和劳斯莱斯吧,不够再补充啊,婚后财产归女方所有。”
“去你的,我还没同意嫁我女儿。”母亲拧了下季父的胳膊。
“别管了,让他们俩好好待着,我们这两个老家伙就先走吧,”季父拉着母亲走了,离去时还不忘回头对季屿川小声说了句,“小子,记得做好安全措施。”
我听见了。还听得很清楚。
脸烫得厉害。
母亲又拧了季父一下,她回头蹙眉朝我们叮嘱道:“不许乱蹿房间。”
季父直接把她给扛走了。
她的话等于白说。
晚上,洗完澡出来,我放了点音乐,正擦着头发,季屿从后面抱住了我。
他把头埋在我颈脖里闻了闻。
“好香。”
“别闹。”
“在国外想你许久了,窗外又是一轮新月,情不自已。”他认真道。
我不由得低头笑了下,回头朝他看去,大概神情有那么点儿温柔,或许还有点儿调皮。
季屿川有片刻的晃神。
他说:“大溪地日落时分的霞,也是这般的美。”
说着,他吻了吻我的眉心,将人抱到沙发上,替我把头发吹干了。
躺在床上,一瞬间,我们谁也没有说话。
只是静静地躺着。
异国的夏日午夜,华城的铁树银花,无数光景从我们眼中川流而过。
风徐徐地吹。
我下意识地侧了个身,落进季屿川怀里,他将我抱满了。
月光很深很静地从我们身上流淌而去。
季屿川用下巴蹭了蹭我的脸颊。
他的眼神清朗温和,令人想起月夜的荷塘。
他说:“六年前,有月亮的晚上,我就在幻想这样的时光。你那时为何不肯答应我?”
“抽烟打架、飙车逃课,样样不落……我以为你是纨绔子弟。”
他笑了笑:“那后来为什么又改变看法呢?”
“后来才发现,那个少年的拳头里面护着个混蛋,却闷着什么都不说,攒够了三年的勇气才敢来告白。”
而我一句话,摔了真心,挫了尊严。
房间里循环到了鲍勃·迪伦的歌。
“不知道假如我见了你,会吻你,还是杀了你……”
季屿川吻了过来。
他说,当时想杀你的心都有。
13.
那晚的事,顺理成章。
像是这些年里的爱与恨,情与仇,季屿川的动作起初很温柔,温柔得令人想落泪。后来却发了狠,变得很凶,很野,一下一下地撞了过来,带着点邪气。悬崖、谷底、巅峰。剑走偏锋。一浪一浪的快乐与痛,想哭,想唱,想尖叫,真有几分醉生梦死的味道。
次日醒来,我的腿简直是有些发软。
季屿川他搂着我的腰。
铃声响了,宋珩的电话打了过来。
季屿川捞住了我的手:“不许接。”
“今天要去检查牙齿。”我说。
出了声,才发现自己的嗓子已经哑得有些没谱。
季屿川临时改变了主意,他说:“接吧。”
“喂,宋珩……”
那边沉默了几秒。
宋珩说:“还过来吗,今天?”
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悲伤潮湿。
“怎么呢?”
“没什么,来吗?”
“嗯。”
按安排肯定是该过去的。
但是宋珩很意外地问了我。
季屿川今天也很奇怪,他替我挑好了衣服才去公司。
临走前他说:“不许照镜子。”
美得他。
天上下了点小雨,赶到科室时,宋珩正在给器械消毒。
苍白的灯光飘了下来,铺出一重薄薄的阴影。
他的侧影令人想起阴雨绵绵的江南。
“真的没事吗?”我问。
“嗯,先去上面躺着等会儿。”
宋珩今天的动作很慢,他失神地穿上大褂,戴上帽子与手套,看上去有些疲态,或者说是落寞。
开了灯,他俯下了身,微凉的手指托住我的下巴,忽然间就停住了。
目光落在我的锁骨处,受了伤般,一触即离。
“昨晚睡得很晚?”
“嗯。”
“以后……不许熬夜了。”
“就算熬,你不是也不知道?”
宋珩只是笑了笑,俯下身,取了探针,将口镜探入我口中。
“第二颗磨牙的牙神经坏掉了,种颗牙,保存牙槽骨和牙龈?”
“嗯。”
“今天常规检查后就将种植体植入颌骨?”
“愈合周期4-6个月,往后隔一月复查一次,隔一年维护一次?”我伸手摘下了宋珩的口罩,有点捣乱地看着他。
他无奈地笑了,索性将手套也取了下来,解了大褂的扣子,坐在一旁安静地看着我。
“宋珩,你状态不对。”
“嗯。”
“今天不看牙了。”
我跳了下来,拉了下他的手,“我们兜风去。”
宋珩的身体一僵。
我意识到不对的时候,他干燥的手已经握紧了我的手掌。
14.
“睿智老人,上来。”
我一脚跨到机车上,笑着将头盔递给宋珩。
他抬头望了一眼天,说:“哦,小朋友,下雨天,可不敢这么野。”
我用手抓了抓空中飘着的雨珠,说:“没什么的嘛,大不了磕坏了牙你再种一颗。”
“上来嘛。”我拍了拍后座,重复了一遍。
宋珩用双臂环住我的腰,头靠近我的肩膀,他说:“大概你以为我想谈的是柏拉图之恋。”
我将头盔扣上:“大概柏拉图之恋你也不会谈。从前你说男女间的爱与性不过是人类进化本能的驱使,而你是无性恋,注定了是一辈子的单身贵族。”
宋珩含糊地笑了笑,注视了我几秒,目光从我的唇瓣擦过,他往前靠近了一点,看上去像是把我拢进了怀里。
“开车吧。”
“嗯。”
我们一路疾驰上了盘山公路,机车发出轰轰的响声。
雨珠淅淅沥沥的飘来,清爽的凉意滑过血液,无数的琐碎与庸常从体内抽离,撤去,再撤去。极致的舒适。
我深深地吸了口气,闭了会眼。
“宋珩,天气预报说雨不会停,可是我想去山顶,你呢?”
他笑了笑,从后视镜里看着我,眸子里有一种令人想躺进去的温柔。
他看上去很安静,并把声音放得很低。
他说:“都听你的,公主。”
半山腰时,果然下起了滂沱大雨,树叶发出哗哗的扑簌声。
我换了挡,雨打在脸上有种受虐的痛快。
有点疯狂,但感觉极妙。
我们在山顶的木屋旁停了车,取了头盔,我扬起眉看向宋珩,问道:“感觉怎么样?”
“我是说,你还悲伤吗?我知道的,你今天情绪不佳。”
宋珩手上动作一顿,他眼里的眸光缓缓流动了一下,有些温暖。
他将我垂落的头发轻轻绾到耳朵上。
“很乱吗?”我问。
他摇了摇头,柔和地笑了一下,笑底下有些坚硬的东西。
他说:“你现在美得有些令人恼火。”
“哦?你是说落汤鸡吗?”我打趣道。
宋珩没说话。
他的目光静静地拂过我的身体。
沉默了一阵,许久,他用手盖住了我的锁骨,往前走了一步,肩抵着我的肩。
他俯在我耳边低声道:“大概你不知道,我不愿当绅士了,想做一回暴徒。”
“嗯?”
宋珩没有回答我,他走进了屋子。
15.
这是间民宿,剩了一个单人间。
泡了会澡,在蒸汽里熏了一时,我的皮肤已有些微微泛红。
见我出来,宋珩轻轻地咳了下,避开了视线。
他递来一杯热茶,拿着浴巾进去了。
“别感冒了。”他说。
我接过茶,抬眸看向他:“嗯,那个,晚上山上气温低,地上有些潮,你打地铺不会冷吗?”
宋珩脚步一顿,睫翼稍微颤了下:“不会。”
他说服务员刚刚来告知,山谷突发泥石流,我们今夜无法回去了。
我给季屿川打了个电话。
那边沉默了几秒,随后传来钥匙的声音。
“吹干头发,穿好鞋,我来接你,现在。”
“路上危险,别来。”
“忘了自己晚上怕雷?”
“宋珩在这里。”
“你是他喜欢的类型。”
“不会的,他……”
季屿川截断了我的话:“所以,你让我看着自己的女人躺在别的男人怀里?”
“没有……”
他已经挂断了电话。
我有些担忧地坐在床上,给发消息他也没回了。
纠结了半天,还是放心不下,我敲了敲浴室的门:“宋珩,我出去一趟。”
里边的水声迅速停了,宋珩单系着条浴巾走了出来,身上的泡沫还未冲干净。
他擦了擦脸上的水珠:“去哪里?”
“季屿川要来,我去看看。”
“雨下得这么大,穿着这么一身?浴袍?开车、走路?”
“嗯。”
“想都别想。”
宋珩把我抱了起来,放在盥洗台上。
“你是不是以为我不会生气?”
我沉默了几秒,垂下了眸,闷声道:“早知道我就不来了。”
宋珩托住我髋部的手一松,许久,他错开了目光,平静道:“他不会来的。”
说完,他放开了我,走到淋浴下,开了水。
他说:“换作是我,那便自己嫉妒着、焦灼着,怎么舍得让你担心?”
16.
中途,季屿川果然折回去了,他打电话过来,顿了几秒才开口。
“路况一好就接你回家。”
我轻轻地应了声。
“晚上打雷了,不要怕,我在这里。”
“嗯。”
宋珩接过了电话。
季屿川沉默了一阵,他说:“你最好别动其它心思。”
宋珩没说话,他看了我一眼,单腿盘到我旁边,挑起我的下巴,低声道:“怕雷?雨天还敢骑车上山?”
我不自觉地咬了咬唇,低下了头:“……这不是你心情不好吗?”
宋珩注视了我好一会儿,他掐断了电话。
“你说我早点承认自己的心意该多好?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不止朋友关系?”
“嗯?”
“我得意思是,我现在想吻你,如果你愿意的话。”
像是“轰”的一声,无数的片段和细枝末节叠到了一起。
一瞬间,我脑子里有些混乱不堪。
该早点看清楚的。他是匹狼。
我看着宋珩,往后退了退。
“抱歉。”
他擒住我的双手,将我推倒在床,欺身吻了过来。
“跟我在一起。”宋珩哑声道。
“不单是想与你进化下一代的意思。”
说着,他拂开了我的浴袍,手往里部探去。
我不自觉地一颤。
“宋珩,不要让我讨厌你。”
他停住了,顿了几秒,忽而就笑了笑,撑到我前面:
“你对我,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么?”
我抬头看了看他,睫翼颤了下:
“没有。”
屋子陷入更大的寂静之中。
外面的雨声哗哗地下,窗外闪过几道雷电。
许久,宋珩起了身,往浴室走去。
如同一只剥了壳的河蚌,他的气势一点一点地弱了下去。
我垂下了眸,平静地说道:
“你若是有那么点喜欢我,一开始便不该骗我,说自己是无性恋,不打算谈真恋爱。”
“我当真了。”
“我不知道,我们之间,是否还能做朋友。”
宋珩的脚步一怔,手中的浴巾缓缓落地。
雨声,更大地落了下来。
七零八落,洒了一地。
【尾声】
那天,季屿川还是放心不下。
他瞒着我上了山,我问他怎么来的,他愣怔了一瞬间,随后摇了摇头,说我也不知道,好像是单想着你便能够跨越千难万险似的。
我看着他笑了,笑着笑着便画出这些年来他的疯狂、偏爱与不顾一切,泪落下来,记忆里的梅花落满了三山。
我吻了吻他的唇角。
以后这样的事,不许再做了。
嗯。
我们驶过了那些说话句句要打靶心的年月。
后来,宋珩去国外访学了,我们至此再没见过。
直到我结婚那天,他跟我发了条消息。
没给你种好牙便离开了,抱歉。
没事,现在已经完全没问题了。
那,新婚快乐。
嗯,愿你在国外安康,顺问夏安。
两三缕阳光从窗外斜斜地打了进来,白色的鸽群飞过千屋万檐,薄雾褪去,琥珀色的世界浮了出来。微风细细碎碎地拂着。
再过个两三点钟,季屿川该来了。
我朝路旁看去,栀子花开了,新一季的荣枯拉开了帷幕。
(完)
再次声明:转载文,如有侵权,联系后删除。
本文来自作者[恨风]投稿,不代表发展号立场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fastcode.vip/yxjl/202510-20265.html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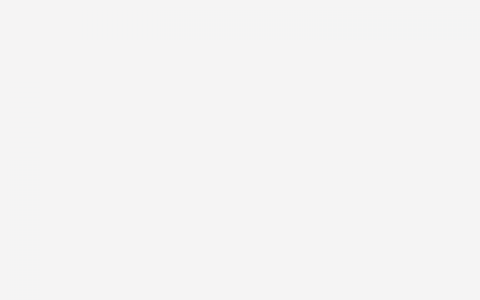
评论列表(4条)
我是发展号的签约作者“恨风”!
希望本篇文章《反刍技巧微乐斗地主开挂有挂吗(详细开挂教程)(你不该骗我的完结文)》能对你有所帮助!
本站[发展号]内容主要涵盖:国足,欧洲杯,世界杯,篮球,欧冠,亚冠,英超,足球,综合体育
本文概览:我妈改嫁了。推开门,遇见季屿川的瞬间,我的心跳停止了,脑子里空白一片。高考后他向我告白,我平静而冷淡地看向他。“我很讨厌你。”我说。他似是被定住了一秒,随后便自嘲地笑了笑,试着...